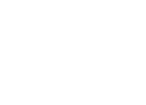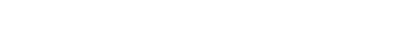编者按
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作为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,上财的百年发展史既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曲折发展的缩影,又是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在一所高校的生动反映;既是一部承载着历代上财人励精图治、薪火相传的奋斗史,又是一部不断激励当今上财人追求卓越、勇攀高峰的智慧宝库,是我们开展“四史”学习教育的宝贵资源。通过“上财人的四史故事”系列,让我们聆听历代上财人的讲述,聆听属于上财人的故事和红色记忆,感受历代上财师生与党同行、与国共进的家国情怀和奋斗精神。
口述者:叶品樵
口述时间:2016年12月5日
口述地点:福建省福州市叶品樵校友家
人物介绍:
叶品樵(1933-2018),福建闽侯人。1953年因院系调整从厦门大学调整进入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就读,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55 年毕业后留校工作,任工业经济系助教。1957年调往厦门大学经济系工作,历任厦门大学经济系主任、厦门大学教务处副处长。1983年调任福建省高等教育厅副厅长,1986年任福建省教育委员会副书记等。1994-1996年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。

叶品樵校友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史座谈会(2017年11月12日)
问:您是怎么来上海财经学院读书的?
叶品樵:我离开上海财经学院已经整整60年了,一轮甲子过去了。我在上海财经学院4年,从1953年到1957年,当了两年学生两年助教。我是1952年考进厦门大学的,学财经。当年,厦门大学财经方面一共是156个学生,有6个专业,包括政治经济学、会计学、统计学、财政金融、国际贸易、企业管理,我选择的是企业管理。当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已经开始了,我们想将来毕业到工厂里工作是很好的,所以当时有很多人争着学企业管理。我记得一个系只有一个班,二十几个人,是小班。不久,全国院系大调整,把厦门大学办得非常好的工科撤掉,并到浙大、南工,有的甚至合并到武汉。这样,企业管理系就很难办下去了,因为我们系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与工业技术相关的课程,比如工业技术的切削原理、制图认图等。厦大工科并走后这些课就没有了。我们企业管理专业,就是看你工科方面学了多少,工科方面的知识有多少。因为企业管理系毕业的学生到工厂做计划工作、生产调度工作,都是要基本看得懂人家给你的图纸,厦门大学工科调整了,企业管理系也就得调整。当时有统一的规定,华东地区的财经系全部并到上海财经学院。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除了我们企业管理系,其他系都没并走。
还有一个情况。通常大学本科都是四年,但是解放初期为了第一个“五年计划”,学生要提前一年毕业,所以我1952年进校的时候有三个年级,等一个年级毕业走了,只剩下两个年级。院系调整的时候,厦门大学财经系科没有老师带着我们去上海财经学院。当时我们系的学生当中也没有共产党员,只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,由11名团员成立一个团支部,我是团支部书记。后来,复旦大学的苏东水担任组织委员,还有一个宣传委员,我们就三个人。等苏东水毕业了就又剩下我和一名宣传委员。学校让我带队,介绍信等很多材料就是由我带去上海的。
问:你们是怎么从福建到上海的呢?
叶品樵:那个时候很艰苦的。我们先从厦门到福州,然后从福州再到上海。在福州闽江坐船,不坐船就要走山路,山区有很多山路,更难走。我们坐船到南平,换汽车到建阳,住一晚上,第二天从建阳坐汽车到上饶,然后再从上饶转火车到上海。回程的时候,是从上饶坐汽车到建瓯,再从建瓯到南平,然后坐船到福州。1953年我们不是在福州集合一起去上海,而是大家按规定时间在上海集合后一起去上海财经学院报到。

叶品樵(后排左一)与工业经济系同学在上海财经学院四达路校门口合影(1955年8月)
问:您还记得院系调整时上海财经学院的情况吗?
叶品樵:好像我们厦门大学是最后一家并过来的。那个时候学校有解放楼,旁边是一个操场。开并校大会时,华东各个单位来的人派代表到主席台就座,厦门大学就是由我代表。别的大学、学院都是老师,只有我是学生。
当时给我们上课的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。上海财经学院名教授很多,比如我们工经系主任孙怀仁。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,写了很多书。他很有特点,年轻人在他旁边吵吵闹闹,他自顾自在那备课,毫无反应,也不说别人。而且孙怀仁讲课从来不用稿子的。
另外,说说我入党的亲身感受。我是由许浪璇(当时的学校党委副书记)当介绍人的。我从福建到上海有很多事情都不懂,许浪璇问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,我说,我看了两篇文章很感动,一篇文章是《党员登记表》, 还有一篇是《老水牛爷》,就觉得我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。许浪璇一下子脸沉了下来,看两篇文章就可以参加共产党?后来,他拿出党章和其他几本书,让我回去看完再来。
我们的教务长是吴承禧,副教务长有两位,其中一位是许本怡。当时会计系有位娄尔行教授,他有一个“凭证整理单据记账”的成果,还因此在全国出了名。会计系的龚清浩教授资格非常老。我还记得工业经济系有马家骅,他西装革履,冬天穿大衣的。
问:您对母校还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地方吗?
叶品樵:主要是对母校的深深感激。从我个人来讲,母校给了我三样东西:一是入党,二是当了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,三是留校当了助教。1954年5月25日我在上海财经学院入党。1954年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,与会代表约两三千名。其中,大学生代表三人:上海交通大学一名男生,上海财经学院一名男生,上海戏剧学院一名女生。上海财经学院的名额就是我。通过代表的事情,说明院系调整后的上海财经学院非常庞大。1955年,我毕业留校。我们班很多人从福建来,也有不少上海人,毕业后都想留上海,不想去远的地方。毕业分配有留校的名额,但我填报的志愿是去北京。当时我已经入党了,是团支部书记,成绩也不错。我第一志愿是想去北京,北京是首都。如果北京不能去的话就是第二志愿去东北地区,东北当时是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地方。要是东北不能去的话我第三志愿是西北,去条件最艰苦的地方。结果,我留校当助教了,可能是因为大学二三年级的时候,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,可能被老师们看中了吧。学校留我下来,给了两个选择,在宣传部或团委工作。但是,我想留在工经系做老师,后来就留在工经系了。

叶品樵(右一)与同学在校园里合影(1950年代)
问:您当人民代表期间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事吗?
叶品樵:我们一起开会的有很多名人,比如禇凤仪副院长。我是第一届、第二届的代表,那个时候一届是两年。1956年第二届代表大会的时候,没有北四川路区了,改为虹口区。我作为人民代表,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。上海市一路电车存在了很长时间,现在没有了。它是从静安寺到虹口公园的,实际上在北四川路已经停下来了,就在那里拐一个“Y”字形的弯。当时,我们代表团坐了一次一路电车,明明起止站是静安寺到虹口公园,怎么在北四川路就停下来呢? 而且在那里拐一个“Y”字形弯也很不好。于是,我们联合做了一个提案,建议把这个“Y”字形的弯改一下。上海市对此很重视,想处理这个问题。但那里有警备司令部的楼,到虹口公园要从那栋楼过去,车辆震动会影响设备。我们就去勘察,提议从北四川路直接开一条小路,经过鲁迅故居。大概在1957年,这条路通了,通到虹口公园,我离开上海之前特地去坐了一次,因为这个提案是我们提的。
问:您留校任教的情况是怎样的?
叶品樵:我留下当助教的时候,第一个目标不是自己钻研成果,而是到人大学习一年。当时各个财经学院的助教老师都要轮流去人大学习一年。到人民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学课程,就是把人大的课程原封不动搬回来,能把课教好就不错了。后来做了财大校长的张君一,当时是学校办的厂长学习班的讲师,我跟着听他的课,给他当助教。
问:那您又是怎么离开上海财经学院的呢?
叶品樵:1957年上海财经学院要跟政法学院合并,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。当时厦门大学统计方面需要一些教师,工经方面也需要人。我是从厦门大学来的,觉得是一个回厦门工作的机会。就这样我回到了厦门大学。
问:您调回厦门大学之后的工作情况是怎样的?
叶品樵:回去先是做老师。1968年,我是系办公室主任,抓教学业务。1972年我是厦门大学经济系系主任,当了5年。后来,学校把我调到教务处,当副处长。再后来又调去福建省教委,最后回到厦门大学担任校党委书记。
供稿/图:陈玉琴 审稿:喻世红 高冰冰